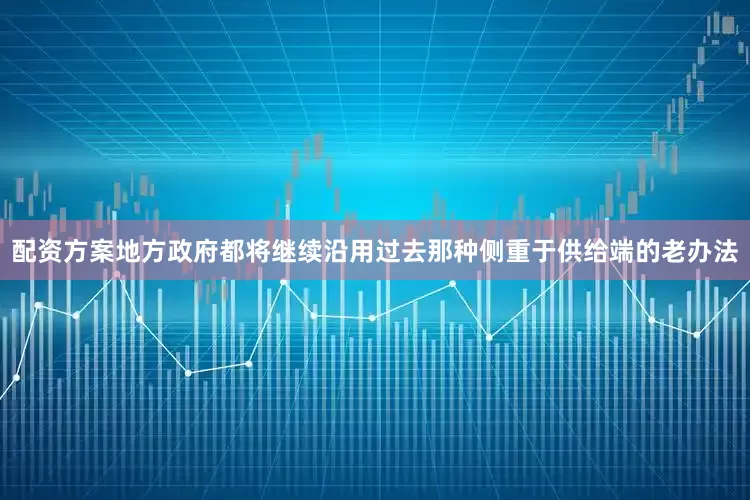在苏联解体前夜,各级官员在生活享受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基于官职等级的特权制度,其核心原则是“待遇随官职升迁而递增”。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所述,全莫斯科大约有四万人能够享用各种特供商品,且这些特供商品的使用亦遵循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对于部长乃至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高层官员,叶利钦将其地位比喻为“攀登至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一旦达到这一层级,他们便能享有一切特权,“仿佛已步入共产主义”。

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宅邸之中,约40至50名仆役为其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家中每日迎来亲朋好友及食客多达数十位。若将此景象与那些亿万富翁或皇室贵族的住所相比,或许你并不会感到惊讶。但当这一幕与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生平交织在一起时,你是否会感到一丝不同寻常的触动呢?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莅临莫斯科,并在其《莫斯科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他在文中感慨道:“那支由国家与民族守护者组成的伟大队伍及其领导者,正不遗余力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独特的阶级”,“而民众则仍旧为了求得一片面包、一缕空气(住所)而陷入艰苦的斗争”。罗兰不禁感到震惊,他发现就连无产阶级的杰出作家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般供养。他观察到苏联已悄然形成了“特殊的特权阶层”和“新兴的贵族阶层”。
特权阶层的形成,源于制度设计的安排。斯大林凭借其手中所掌握的“无上权力”,尤其是对干部分配的掌控,创设了官职等级名录体系。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确立了选拔与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体制,该决议明确了三种官职等级名录的任职资格。在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致有3500个至关重要的领导职位,涵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的首脑、托拉斯与辛迪加的领导者,以及大型工业企业的管理者等;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则囊括了各部门、各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应职务;而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专注于地方层面的领导干部。
若您有幸跻身名录之列,便意味着您已被“特别安排”,得以享受特权阶层所独有的生活方式。
若您目前尚未名列其中,那么您或许需要考虑寻求其他途径。
至1924年初,中央委员会已确立的领导干部总数达到了13,163人。各地方组织亦自行设定了相应的官职等级清单,例如乌拉尔州委便明文规定本州领导干部的人数为1,066名。然而,地方级领导干部中,仅关键职位需由中央委员会进行任命。
官职等级名录囊括了至关重要的职位与职务,所有候选人均需经中央委员会的预先审查与批准,其职务的解除亦须征得中央委员会的认可。位于这一权力金字塔之巅的是斯大林。
权力日益趋向集中。随着联盟部级单位的增多,数量已高达160个,而各个行政部门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种类繁多,规模庞大,数量超过20万种,条款累计达千万之众,几乎涵盖了一切日常行为。行政命令体系虽不断强化,却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这无疑导致了国家机构的膨胀和官僚作风的盛行。至1985年,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副部长人数已突破800人,审批一份普通文件往往需时数周,甚至长达一两个月。
官职等级名录,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名词,有幸列入其中的苏共领导干部逐渐转化为“红色贵族”——拥有个人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的特殊社会集团。
工资与“钱袋”制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享有一种特殊待遇,即特定的工资制度。1945年4月,苏联政府正式规定,对于在机关、企业或团体中担任关键职务、具备深厚学识和丰富经验的人员,将实施这一特殊的工资制度。该制度下的薪资通常设定在2200至3000旧卢布之间,而最高额度则可达到4000至5000旧卢布。
该特定工资数额随后又有所提升。然而,这一增长的部分并未体现在工资条上,而是与工资一同,以封口的小纸袋形式发放。此乃苏共历史上所谓的“钱袋”机制。
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与作家丘耶夫在1969年至1986年间展开了多次对话,在这些交谈中,他们讨论了工资及“钱袋”制度的相关议题。莫洛托夫透露:“我此刻难以确切告知自己的薪酬数额,因其已多次变动。此外,战后得益于斯大林的提议,实施了‘钱袋’制度。这种封存的小包被用来向军事及党的领导人输送大量资金。诚然,这种做法并不完全正当。金额之巨,程度之高,都超出了合理范围。我对此并不否认,因为我并无权对之提出任何异议。”
秘密地将款项装于信封之中,递送给各级官员,每月的金额依据职务高低,大致介于数百卢布至数万卢布之间(需注意,此处涉及1960年币制改革前,旧卢布与新卢布的兑换比例为101)。这些资金无需缴纳任何税费,甚至连党费中也未曾包含在内。领取“信封”的人员需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一旦泄露消息,将面临严厉的惩罚。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币制因素的影响,斯大林时代一位部长的月“信封”金额大约为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这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然而,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800美元。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政策予以摒弃,并下定决心对干部特权体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他力主实施领导干部的轮岗制度,同时大幅下调了高级官员的薪酬。1957年2月,苏联方面向我国驻苏大使馆透露,自3月1日起,苏联将下调高级官员的工资。新规定中,政府部长每月最高工资定为8000卢布(以旧卢布计),副部长为7000卢布,部务委员为4700卢布,司长为4500卢布,副司长则在3000至4000卢布之间。党中央各部领导人的工资也有所下降,但相较于政府部门,仍保持较高水平。此次工资下调的幅度相当显著。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为例,其工资由原来的15000卢布降至5000卢布。与此同时,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仅为300至350卢布,即便高级官员的工资下调后,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依旧悬殊。
赫鲁晓夫的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成效,最终导致了其政治生涯的终结。
位居官场显赫地位的高官们,纷纷力挺废黜赫鲁晓夫,并将勃列日涅夫推上权力之巅。勃列日涅夫迅速对赫鲁晓夫的政策予以否认,他采纳了依赖特权阶层的策略,并强化了领导干部的继任原则,修改了领导干部的轮岗机制。他不仅恢复了赫鲁晓夫曾废除的部分高级干部的特权,更增添了一系列新的特权。
根据现有资料,前苏联的领导层在物质享受上无疑是“应有尽有”,其与普通民众的薪酬差距甚至高达五十倍以上。机关领导干部每月还可获得相当于工资一倍以上的额外补贴,且职务级别越高,补贴金额也越丰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政治局成员已近乎达到“各得其所”的境地。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前苏联的都城莫斯科。每到周末,位于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段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便会呈现出一幅独特的景象:擦得发亮的“伏尔加”轿车整齐排列,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司机们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后视镜上,他们无视交通规则和警察的劝诫,满不在乎地将车辆随意停放。他们的视线始终不离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楼的入口。

小白桦商店
这座土黄色的建筑,其窗户均以不透明材质覆盖。门前,一块醒目的牌子昭示着,1919年,列宁曾在此发表激昂演说。另一块牌子上则赫然写着“领证处”。然而,并非任何人都能在此轻松领证,唯有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方能获得资格。在这座隐秘无招牌、仅凭特殊证件方可踏入的商店里,男女顾客们均手提大包,乘坐汽车匆匆离去。他们皆是苏联的精英阶层,专程至此,只为选购那些寻常人难以触及的珍品。
众多秘密商店专为苏联的精英阶层提供服务,迎合了“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们的需求。这些独特的商店允许上流社会人士选购国内难得一见的美食佳酿,诸如鱼子酱、蝗鱼、鲑鱼以及出口级的伏特加,此外还有“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如法国的白兰地、苏格兰的威士忌、美国的香烟、瑞士的巧克力、意大利的领带、奥地利的皮鞋、英国的厚呢、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晶体管收音机和日本的录音机等。
这正是令莫斯科寻常百姓心生向往的“小白桦”商店。
位于莫斯科最大国营商店“古姆”三层的一个隐蔽角落,藏匿着名为“100号分店”的神秘空间,该店专为上层人士所设。而在军人商店的地下室深处,则存在着一个仅对军官开放的隐蔽商店。此外,莫斯科街头遍布着专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各类商店,包括特殊裁缝店、特殊理发店、洗衣店以及化学洗染店等,数量多达一百余家。
苏联某位记者曾言:“对于那些位居高层的人物而言,共产主义的建设早已圆满完成……”
这便是苏共高级干部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为了维持这一独特优待,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前苏联的著名伏特加酒——“首都”牌,正是在德军围困、粮食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于列宁格勒这片土地上诞生的。
1942年,德国军队将列宁格勒严密封锁,宛如铁桶。居民们饱受饥寒之苦,饥饿至极,步履维艰,仿佛行走的幽灵。而在同一时期,列宁格勒知名酿酒师斯维德利在酒厂的实验室里辛勤劳作,汗水淋漓。他正遵从上级的秘密指令,精心酿造“首都”牌伏特加。
这珍贵的粮食,经过精心酿造,化身为风味独特的上等美酒——它并非什么击败法西斯的神秘武器,而是专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市委的领导层所预备的“特制佳酿”。
若能将这些粮食节省下来,或许便能挽救无数市民的生命。
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前任所长阿尔巴托夫揭示了斯大林时代的特权体系。
他笔触细腻地描述道:“此制度之下,等级森严,自政治局委员至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乃至各局首脑,各层级皆拥有专属特权。战前,享有这些特权者寥寥无几,然而所获得的特殊待遇却相当丰厚。”战后,随着配给制的废除,特权迅速蔓延,“从斯大林至集体农庄主席,不论级别,皆可享受黄金地段的高级住宅、免费别墅居住权、专属汽车(包括领导人的配偶及子女,有时甚至一人可拥有数辆以供选择)、专职司机服务、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休养所的免费入住,以及大量路费、补助和所谓的‘医疗费’。此外,还有豪华的狩猎活动,无需排队即可在特供商店中选购紧俏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便有数百此类商店),以及各式各样的特殊供应。”
自70年代起,苏联的特权阶层规模显著扩大。
特权的供应体系按照等级严格划分。居于顶层的无疑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他们享有所谓的“克里姆林宫份额”,能够享受到大量的免费供应。在莫斯科,设有专为1930年之前加入党组织的资深布尔什维克开设的配售点,还有为元帅和将军们定制的配售店,以及面向知名学者、宇航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经济型配售店……这些按等级设置的店铺相较于普通商店,商品种类更为丰富,价格也更加优惠。此外,还有专为特权阶层提供服务的特殊服装店、特殊理发店、特殊食品店等。例如,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设有专门的内部商店,专为高级干部提供紧俏商品;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设有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区,仅供政府副部长、州委书记、大城市市委书记及以上级别的高级官员购买商品;而中央百货商店的45号售货部则是为较低级别官员设立的购物区。众多政府机关向官员发放“特殊配给卡”,此卡不仅是进入特殊商店的通行证,还标注了可购买商品的金额,级别越高,可购买金额也相应增加。除此之外,“小白桦”商店销售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和市面上难以觅得的稀缺物品,仅限于持有“卢布证券”的人士购买。所谓的“卢布证券”,是指通过外汇兑换的特殊卢布,只有那些有途径的官员、外交官、记者等才能定期获得。

叶利钦
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叶利钦披露的特权现象不仅更为严重,而且描述得更为具体。在苏联解体之前,各级干部在生活中享受的等级化特殊待遇已经演变成一种制度,其核心在于“一切皆由官位高低而定”。据他所述,全莫斯科约有四万人享有各种特供商品,且这些特供商品还分等级。至于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别,叶利钦将其称为“攀上党的权力金字塔之巅”,此时,他们便能享有一切,“仿佛已步入共产主义!”他以讽刺的口吻如此评论。鉴于当时人们的需求欲望普遍强烈,叶利钦指出,在苏联“共产主义只能暂时为寥寥数十人实现”,“少数人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而广大民众则仍在贫困的泥潭中挣扎”。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回忆起1983年的情景,当时他刚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次日便被配发了高级轿车。然而,当他提出更换为较低档次的车型时,却遭到了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严厉斥责,指责他此举是“特殊化”行为,有损机关风气。这位新晋升的高级官员对此言论感到十分震惊。
在1936年,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之旅,回国后便创作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其中对苏联的阴暗面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揭示。
妇女们手捧一块垫着草皮的生肉,站立在路边,向过往行人招揽生意;有的则提着鸡或类似物品,她们是无照摊贩,既无力支付摊位租金,也无需排队等待租赁一天的摊位,一旦执法人员出现,她们便携带货物迅速逃离。在莫斯科,大学生、教师及小职员的生活仍然充满挑战。
苏呼米邻近的西诺卜旅馆,是高官们款待宾客的场所,纪德对其赞誉有加,认为其堪比法国最奢华、最舒适的沐浴旅馆,堪称“世间人类感受到的幸福之所在”。旅馆侧畔,便是一家苏维埃农场,专为旅馆供应食材。然而,越过那道划分农场界限的壕沟,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低矮、简陋的房屋。“那里,四人共居于长宽各逾两米的房间,每月仅需支付两个卢布的租金。苏维埃农场内的饭馆,每餐费用亦是两个卢布,对于月薪仅七十五卢布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奢侈。他们除了面包,一条干鱼便已心满意足。”
纪德以讽刺的笔触描绘道:“这股崭露头角的新兴资产阶级,继承了——我们原有资产阶级的所有恶习。他们刚刚摆脱贫困的泥潭,便对贫穷产生了鄙夷。他们渴望那些久违的种种利益,深知如何攫取并维持之。‘这些人,便是那些享受革命果实的人。’‘他们或许可以加入共产党,但内心深处却毫无共产主义的气息。”尽管当时苏联四处宣扬人民之间的平等、革命战友间的深厚友谊、共患难共富贵,现实却与之背道而驰。
注释
在莫斯科,人们私下流传着这样一个玩笑:"若你在深夜瞥见某机构灯火通明,切莫误以为他们正埋头加班,多半是在琢磨如何将公款化为私囊。" 这段讽刺意味十足的笑谈,虽然略显夸张,却与实际情形颇为吻合。到了1925年,贪污案件的数量急剧攀升,法院审理工作几乎日以继夜,即便天天加班也难以应对。
列宁目睹此般景象,怒不可遏,猛力拍打桌面。随即,他下令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酬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平均水平的上限。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每月仅领取五百卢布的薪资,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然而,这些规定犹如纸糊之虎,根本无法阻挡腐败潮流的肆虐。
冠盈配资-冠盈配资官网-国内正规配资公司-理财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配资方案地方政府都将继续沿用过去那种侧重于供给端的老办法
- 下一篇:没有了